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内生化模型研究
陶军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2000级博士生 100121)
引言:经济增长理论基本问题的提出
以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论述内生增长理论,至少在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内生增长理论并没有已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确切地说,内生增长理论只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德所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本文的目的在于:在这个松散的集合中梳理出主要的脉络,并对其中的一条作详细的说明。[1]
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基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之上,在拉开内生增长理论的帷幕之前,就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作一点小小的铺垫或旁白是必要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经济增长理论本身,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划分为短期和长期增长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着选择哪一类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的问题。短期经济增长指的是在现有资源、技术约束下实现最大的产出,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即生产是否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上进行;其次是产品数量组合效率,也就是生产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上移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长期经济增长指的是生产能力的长期变动趋势,即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向外移动。
按照S.Kuznets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她的人民提供日益增多的经济物品这种能力的长期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以经济长期增长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增长因素在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既然选择了长期增长作为研究对象,以下的问题就不可避免:
1什么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或者说什么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
2在政府的边界之内,政府做什么能够促进增长或者说政府应该做什么去促进经济增长吗?
不同的阶段,经济学家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不一致的,我们不妨看一看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各自的回答:
一、解答一:古典经济学
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而言,经济学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将经济增长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弗兰克?拉姆齐(1928)、艾林?杨(1928)、弗兰克?奈特、约瑟夫?熊彼特(1934)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本成分:竞争性行为和均衡动态的基本方法,递减报酬的作用及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互动,以不断增长的劳动专业化分工以及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发现为形式的技术进步的效果,和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激励的垄断力量的作用。
着重研究长期经济运行规律的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分支学科来说明经济增长问题。但有一点在古典经济理论中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最终决定于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这三者中,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其数量相对固定,理论分析的重点是资本(尤其是人均资本)和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提高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在经济体系中,资本的增加来自于经济主体自身的积累,而决定积累快慢的主要因素在于储蓄率的高低,相应的,分析资本(人均资本)数量的提高对增长的意义就转化为分析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资本效率的提高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涉及到出生率、死亡率与迁移行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则是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2]积累的过程。
Adam Smith (19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注意到各国潜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基本因素有: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效率提高等方面。斯密明确指出,国民财富就是国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总量,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为了增加国民财富,一要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二要增加生产工人的总数。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加强劳动分工;为了增加工人的人数,就需要增加积累用以雇佣工人的资本。亚当·斯密指出了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的三条途径:(1)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2)节约劳动者在不同工作之间的转换时间;(3)利于“简化和节约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不难看出,如果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这三条途径“翻译”成现代经济理论中的术语,那么它们分别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内生技术进步”(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在Adam Smith的基础上,David Ricardo(1817)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进一步提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土地和其他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可能导致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为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需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技术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虽然Adam Smith把劳动分工放在了开篇的位置,但在马歇尔之后,劳动分工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上就再也没有享受这样的地位[3]。一直到1928年,艾林?杨发表他那篇伟大的《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劳动分工在主流经济学中整整消失了150年。艾林?杨的洞察力并没有很快地融入经济学主流,因为递增报酬与大多数经济学家脑海中的竞争均衡观念始终难以调和。这种状态到了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的经典论文(Dixit and Stiglitz, 1977)发表之后才有所改变。这篇论文用垄断竞争均衡框架讨论了产品种类与数量之间的权衡问题。后来论文中表示多样化消费偏好的D-S效用函数形式被艾塞尔(Ethier,1982)移用到生产技术上,用来表示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收益。这些研究为劳动分工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发展做了技术上的铺垫。
因为古典经济学主要强调经济自身的和谐运行,将经济增长看成经济和谐运行的必然结果,所以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古典经济学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二、解答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伴随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形势而出现的着重研究经济短期运行规律的Keynes经济理论使得人们对古典经济理论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理论的研究重心基本上也从长期经济运行规律转到短期经济运行问题。通常认为,Keynes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萧条问题。Keynes(1936)基本没有涉及经济动态学和经济增长的问题。为使Keynes经济理论具有一般性,就需要考虑如何在Keynes经济理论的假定基础上说明经济增长的问题。这样,如何将着重静态分析的Keynes经济理论动态化就成为Keynes经济理论一般化的重要课题。[4]
Harrod(1939)和Domar(1946) 试图在Keynes分析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他们采用在投入之间缺乏替代性的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体系的增长是内在不稳定的。
Harrod(1939)从保证劳动完全雇佣的角度出发, Domar(1946)从Keynes理论动态化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基于Keynes经济理论的经济增长模型。虽然其经济增长模型的各自出发点不同,但两者的结论是相似的:实际增长率、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由于使得实际增长率和保证增长率相等的资本系数、储蓄率和劳动增长率等是事先相互独立确定的,实际经济活动既不可能保证三者始终处于理想的比例关系,又不可能使其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难以实现的。在出现实际增长率、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不一致时,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并不具有自稳定性。具体而言,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不但不具有自行纠正实际增长率和保证增长率偏离的机制,而且还有将其偏离效应不断积累的机制。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对现实经济增长问题不具有足够的解释能力。
通过对Harrod经济增长模型的固定资本系数假定的修正,Solow[1956]和Swan[1956]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
Solow在他1956 年划时代的文献中,指出了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他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放松这一假定后,Solow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5]
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基于如下一般假设:(1)技术水平持续不变;(2)生产函数中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3)储蓄率外生;(4)劳动供给外生,并以固定速率增长。
Solow-Swan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了不变规模报酬,对每种投入的报酬递减,以及投入之间某种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这种生产函数与不变储蓄率规则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个极为简单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
生产函数的新古典性质造成了Solow-Swan模型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解释力的匮乏。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我们所提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在缺乏技术的连续进步的情况下,Solow-Swan模型的一个预测是,人均增长将最终停止。这个类似于Malthus和Ricardo所做出的预测来源于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从技术推理上说无疑是正确的。但这显然不符合经济现实:我们已观察到正的人均增长率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或更长,而且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NP增长率的差异。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人均资本更少的经济(相对于其长期人均资本而言)趋于有更高的回报率和更高的增长率——导出了Solow-Swan模型的另一个性质: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长期或稳态位置越低,增长率越快。换句话说, 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要快于高收入国家。但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并不能证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这一结论。在1960—1989年30年间,低收入国家增长率最低,高收入国家次之,而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率最高。
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家认识到了这一模型缺陷,通常他们用假定技术进步以一种外生方式发生来对之进行修补。[6]这一假设可以把理论与一个正的可能不变的长期人均增长率调和在一起,同时仍保留条件收敛的预测。然而,明显的缺陷是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被一个模型外部的因素——技术进步率所决定。(产出水平的长期增长率也依赖于人口增长率,另一个在标准理论中是外生的因素。)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增长模型,它能解释一切,却独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7]
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政府部门的评价显然带有古典主义色彩。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政策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率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试图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分散经济不但可以实现静态帕累托最优,而且能够实现动态帕累托最优,“看不见的手”将引导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路径移动。[8]
三、解答三: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1、储蓄率内生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和Koopmans(1965)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
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
2、劳动供给内生
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9]。
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
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 Ehrlich and Lui(1991), Rosenzweig(1990)讨论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内生技术进步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
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
1要素报酬不变: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
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性质是资本报酬不再递减,其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修正在于将技术因子A看成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决定了资本的净增长上限必然为零,所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资本投入量的上限,从而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的增长也等于零。如果能够避免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出现,则有可能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能够持续增长。
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限不为零仅意味着,在一定的范围内,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消失。一个不存在递减报酬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AK函数。Jones,L. and Manuelli,R.(1990);Rebelo(1991)论证了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单部门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与AK模型是一致的。而为了区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许多内生增长模型都假设经济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资源需要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配置。Uzawa-Lucas模型是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代表。
2干中学与知识的外溢
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 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Arrow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一方面一个增加了其物质资本的企业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或边投资边学(learning-by-investing)。另一方面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一个经济范围内的更大的资本存量将提高对每一生产者而言的技术水平。这样,递减资本报酬在总量上不适用,而递增报酬则有可能。
干中学和外溢效应抵消了单个生产者所面临的递减报酬,但社会水平上报酬是不变的。社会资本报酬这种不变性将产生内生增长。
模型的关键在于:第一,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特别地,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导致其知识存量Ai同样增加。第二个关键假设是每一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其他任何企业都能无成本地获得。换言之,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这样一个瞬时扩散过程之所以在技术上可行,是因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Romer(1986)后来证明在这种情形下仍可以在竞争性框架中决定一个均衡的技术进步率,但是所造成的增长率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10]。更一般而言,如果发明部分地依赖于有目的的R&D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的创新只能逐步扩散给其他生产者,则竞争性框架将崩溃。[11]
在这样的现实构架中,一种方法是把不完全竞争整合到模型中去。[12]另一种方法是假设所有的非竞争性研究——一种经典的公共品——都由政府通过非自愿的税收来予以融资。[13]
3人力资本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途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劳动生产要素的引入,使得有关人力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劳动投入是指一般的劳动投入,看不出不同质量或不同技术熟练程度的劳动的投入对于产量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差异,需要对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以说明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Lucas(1988)引入了Schultz[14]和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借鉴Romer(1986)的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Uzawa的技术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Lucas(1988)中,企业能获得的知识的多少不依赖于总资本存量,而依赖于经济的人均资本。Lucas假设学习和外溢涉及人力资本,且每一个生产者都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而非人力资本的总量。不再考虑其他生产者所积累的知识或经验,而是考虑从与掌握了平均水平的技能与知识的平常人的(自由)互动中得来的收益。
4研究和开发(R&D)[15]
技术水平可以被诸如R&D支出之类的有目的的活动所推进,这样的内生技术进步将使得我们从总量水平上的递减报酬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特别是如果技术上的进步能以一种非竞争的方式被所有生产者分享的话。对于知识进步,也就是对新思想而言,这一非竞争性是存在的。
将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中始于Romer(1987;1990); Aghion and Howitt(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chapter3, chapter4)。在这些模型中,技术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些活动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想法、观念耗竭的趋势,那么增长率在长期中可以保持为正。然而由于新产品及新生产方法的创造有关的扭曲的缘故,增长率和发明活动的基本数量趋于不再是帕累托最优。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动,诸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过它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好或坏的巨大影响。
新的研究也包括了技术扩散的模型。虽然对新发现的分析与领先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率有关,对扩散的研究却属于分析后进经济在这一进步过程中如何通过模仿来分享好处。既然模仿比创新要来得便宜,扩散模型预测了一种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预测类似的条件收敛形式。
5、内生增长理论思路小结
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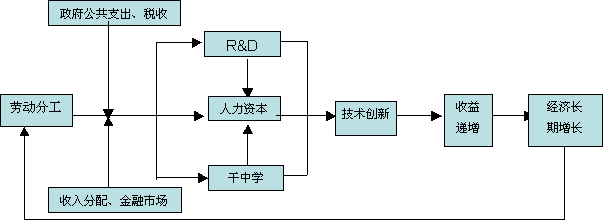
四、内生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内生化
(一)人力资本内生化基本模型
1、AK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寻找能使得资本报酬不再递减的生产函数就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假定(1)储蓄率外生且保持不变;(2)技术水平固定。一个不存在递减报酬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AK函数:
其中Y为产出,A是一个反映技术水平的正的常数,资本K是一个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的广义的资本。这两类资本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从而人力资本可能抵消物质资本最终必然出现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使得资本报酬率不会下降。这样,资本收益不变的假定与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再矛盾。
该生产函数的意义在于:总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形函数。因为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都是正的常数A,所以不存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AK模型假定资本具有不变的边际产品,资本积累过程不会中止,所以,即使经济中不存在任何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也足以保证经济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增长。
AK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长期人均增长率的决定。在AK模型中,长期增长率(等于短期增长率)依赖于技术参数A。A决定了储蓄意愿及资本生产率,它的改进能提高资本的边际和平均产品,从而提高增长率且降低储蓄率。各种政府政策的变化其实等价于A的移动,即我们可以把参数A的解释一般化。
AK模型通过避免长期的资本报酬递减而产生了内生增长。然而这一特别的生产函数也意味着资本的边际和平均产品总是不变的,因而增长率没有呈现出收敛性质。
既保留长期中资本报酬不变的特征,又恢复收敛性质是可能的——这是琼斯和真野惠里(1994)提出的思想。琼斯和真野惠里为了说明资本积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将AK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结合起来,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函数F满足稻田条件。在这个总量生产函数下,资本积累导致边际产品递减,但资本边际产品不是趋近于零,而是趋近于一个正数A。这样,经济增长具有一种过渡动态性,均衡增长率逐渐降低,最终经济将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增长。
琼斯-真野惠里模型说明了资本积累不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品无限降低,但没有说明稻田条件不成立的原因。Rebelo(1991)[16]则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为了说明资本积累足以保证经济内生增长,Rebelo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拥有不同生产技术的部门,因此,同后面将论述的Uzawa模型和Lucas模型一样,Rebelo模型也是一个两部门模型。不过,Rebelo不同意Lucas用外部性和总量生产函数的收益递增说明经济增长的思路。Rebelo认为,只要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线性形式,或者更一般地说,只要经济中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它由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来,并且不可再生要素对它的生产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么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经济将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增长。
由琼斯-真野惠里模型和Rebelo模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国的(核心资本)生产率水平越高,或者消费者的储蓄意愿越强,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这样,各国增长率水平的差异就主要取决于各国经济政策的差异,税率较高国家的增长率将较低,从而,政府应对人力资本或核心资本积累实行税收减让政策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
2、具有物质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对于单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而言,通过劳动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所得到的是同质的产出,不仅可以用作消费,而且可以用于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的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单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与AK模型是一致的。[17]
由于单一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互差异,它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说明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不同,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就应考虑两者的差异而不能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同等对待。这样,就导出由物质资本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生产部门构成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另外,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教育部门实现,而物质资本的积累则要通过物质生产部门实现,因此,又导出物质生产部门和教育生产部门构成的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8]
一般地,前一个模型被视为传统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19]的代表,而后一个模型则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代表。尽管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别:在传统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中,只有一个部门的生产成果进行积累;而在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各部门的生产成果都用于积累。
Lucas(1988) 分析了整个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其研究主要是在Uzawa(1965)的最优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展开的,通常称之为Lucas-Uzawa模型——该模型在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
Uzawa1965年在《经济增长总量模型中的最优技术变化》一文中,运用两部门模型结构,在新古典学派的资本积累框架中研究了如何通过必要劳动投入实现最优技术进步的问题[20]。Uzawa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假定劳动不仅用于物质资本的生产过程,而且也用于与技术进步相关的知识积累过程。技术变化源于专门生产思想的教育部门。假定社会配置一定的资源到教育部门,则会产生新知识(人力资本),而新知识会提高生产率并被其他部门零成本获取,进而提高生产部门的产出。因此,在Uzawa模型中,无须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Lucas(1988)[21]沿着Schultz(1965),Becker(1964)的思路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将Uzawa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
Lucas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具有以下特征:教育部门活动不仅限于人力资本的生产与积累,而且其生产活动只使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无关。[22]
Lucas模型由两个模型组成。第一个是“两时期模型”(Two periods Model);第二个是“两商品模型”(Two Goods Model)。 在“两时期模型”中,Lucas采用类似Arrow(1962),Romer(1986)[23]的单部门模型,将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将劳动划分为“原始劳动”(Raw Labor)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Specified Human Capital),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在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首先采用正式教育的方式,然后通过干中学方式积累——由于该模型中的人力资本完全是在生产过程以外形成的,因此,Lucas又提出了基于“干中学”的两部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两商品模型”。 在“两商品模型”中,所有的人力资本积累方都是通过干中学方式进行。产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即专业化的劳动技能)。人力资本的获得有两种途径——通过学校教育和通过实践中学习,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干中学”获得。Lucas区别了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两种效应: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递增收益,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二)应用理论研究
1、劳动供给、人口与经济增长
1经济增长中的迁移
移民是使一个经济的人口和劳动力发生变化的机制之一。迁移在一些方面与自然人口增长及出生与死亡之差不同。首先,在迁移的情况下,迁入地区的人口增加正好就是迁出地区人口的减少。因此,要把移入和移出作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其次,与新生儿不同,移民带来了他们所积累的人力资本。[24]
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以及 Braun(1993)使用了来自美国各州、日本各地区和5个欧洲国家的数据来估计一股内部的迁移对人均收入差异的敏感性。所得出的净迁移速度对初始人均收入或产品的对数的回归系数平均为每年0.012;
国际间迁移对收入差距的敏感性要比一国之内各地区的更小。Hatton and Williamson(1992)考察了自1850年到1913年间从11个欧洲国家到美国的迁移行为。它们的回归系数基于移入对工资率的比例性差异的反应,平均为每年0.008。
Dolado, Goria and Ichino(1993)考察了1960——1987年间向9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国、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的迁移的构成。假设移入者的学校教育与其接受国的平均学校教育没有系统性的差别,则移入者的教育水平平均为本地人教育水平的80%。Borjas(1992)有美国普查数据得到外国出生者的学校教育水平从1940年本地人的79%上升到1950年的82%,1960年的87%,1970年的94%。
对于一国的迁移来说,移入者与本地人的人力资本之比可能比国际迁移的同样值要高。Borjas,Bronars and Trejo(1992)发现在1986年对美国青年男性而言一州的移入者的平均受教育年份要比该州本地人的平均水平多3%。
2生育选择
虽然大多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假定人口增长率是一个外生常数,但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人均收入、工资率、父母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化都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那种认为人口增长率外生与经济增长的观点是不正确的。Malthus(1798)指出,经济因素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生增长理论意识到Malthus观点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人均收入和父母学历等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趋势做出合理解释。Becker and Barro(1988) 和Barro and Becker(1989)在考虑如何决定出生率的基础上研究了生育选择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父母和子女通过利他主义联系在一起。父母关于孩子数目的决定是与消费和代际让与的选择一块做出的。孩子的生产和抚养是有成本的,但他们所带来的边际效用随着他们的数目增加而递减,或者如果孩子的抚养成本随着其数目的增加而上升,那么模型就能由标准的一阶条件确定出生率。对孩子的选择也与对其质量的决定互动影响,正如把消费和资本存量数额分配给每个人的模型所显示的那样。
Becker和Eric等人建立的微观化模型以一个代表性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假定只有体现知识与技能的人力资本和无需知识与技能的原始劳力资本(raw labor)为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主要分析家庭中由投资回报率决定的父母对孩子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确定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一种经济可能处于两种均衡,在低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很少,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的长期水平处于停滞状态;在高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或保持持续增长,经济也处于长期稳定的增长。受到冲击后两种均衡可以发生转变。两种均衡的分析可以解释世界各国经济的状况。
Rosenzweig(1990)利用不同国家的各种经验证据证实了大多数关于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模型所包含的基本命题: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提高生育率引起的相对成本和回报的变化会相应地使父母改变对家庭规模、每个孩子人力资本水平的决策。他还用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以及外生技术的变化同时导致学校教育投资的增加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节育的昂贵费用成为抑制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但适度的因素。
Becker,Murphy and Tamura (1990)指出,人力资本和内生生育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则是“增长的发动机”,它不仅直接具有生产作用,而且在新知识生产中更有生产性作用。更进一步地,Becker等人指出,生育和人力资本收益都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函数。当人力资本丰裕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较高,而生育率就较低。当人力资本稀缺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较低,因而生育率就较高。因此, 这一模型预见,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会产生不同增长率的多种均衡状态;一种是有持续增长的发展均衡,一种是增长停滞的Malthus均衡。这一模型强调,政策具有积极的效应,如果它们能提供人力资本的刺激的话,从而可使一国摆脱Malthus陷阱走向发达均衡。富有启发性的是,这一模型为战后德国和日本经济复兴提供了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因为战争只破坏了其物质资本。而战前累积的人力资本仍然保存,因而在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引导下,其经济就迅速走上发展之路。
3劳动/闲暇选择
当我们容许劳动力在劳动/闲暇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劳动力与人口之间不再存在固定的关系。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口,劳动力供给变动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工作时间和工作努力程度上的变化的某种组合。通过把闲暇作为效用函数的一个额外自变量引入,Becker(1965);Rebelo(1991);Greenwood and Hercowitz (1991); Benhabib ,Rogerson and Wright(1991) 的研究表明, 劳动/闲暇选择在模型中的引入,并没有改变增长过程中的主要结论。
2、收入分配、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是民主政治。在极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国家,中间阶层的选民在任何时候都很少持有可积累型要素,因此倾向于向要素收益收取高税率。这时候,积累的动力将大大小于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 指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每个时期,选民根据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选择一个再分配税率。拥有低人力资本的选民倾向于一个高的再分配税率。
Alesina and Rodrik(1994)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原始劳动力而言,个人拥有的相对资本禀赋不同。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和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公共开支来源于资本所得税。不同的个人对税率的偏好不同:拥有人力资本的个人偏好于这样一个税率,这个税率能够支撑使得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化的公共开支;而只拥有原始劳动力的个人偏好于更高的税收。
Galor and Tsiddon(1992); Glomm and Ravikumar(1992) 强调家庭的溢出效应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认为对年轻人获得人力资本的投资取决于他的父母的教育水平。相对于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父母而言,教育水平低的父母更加有激励去投资孩子的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总量较低时,只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家长才会觉得在人力资本上投资是值得的。当人力资本总量很高时,投资于教育的回报率之高会使得所有人都有激励投资于人力资本。
3、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生产率和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技术进步之所以可以内生,在于它是这个关系演进的结果。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收益递增,而递增报酬正是这个关系的最基本特点。进入市场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加深的若干个侧面。
在斯密的笔下,分工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多样化,即新行业的出现及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工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即经济的专业化。以Romer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家[25]接受了第一种分工观,将分工视为产品多样化,并由此衍生出水平多样化和垂直多样化内生增长模型;斯密的分工等同于专业化的思想则被Becker、杨小凯等人[26]继承发扬。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Romer(1987)可以说是运用劳动分工解释经济增长的代表。Romer模型的核心是劳动分工与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模型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生产中间产品,另一个部门生产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中间产品有无数多种,最终产品的生产以中间产品作为投入。
假定中间产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如果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就可以通过增加其种类而使得最终产品的产出达到无穷大。
为避免这一问题,Romer假定每一种新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事先投入一定数量的固定成本[27]。固定成本使中间产品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它导致了两个结果:(1)不可能在保持中间产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其种类;(2)中间产品的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的。中间产品总量与种类之间的矛盾使市场范围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当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一种新的中间产品才值得被生产出来。由于规模经济,每种中间产品的生产都由一家厂商垄断,但由于面临着生产其他中间产品的厂商的竞争,该厂商却无法获得正的利润。厂商不断进入中间产品市场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所有厂商利润为零的垄断竞争均衡。这样,劳动分工的演进就被表示为中间产品的种类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展。
与Romer模型相比,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则是从另一条途径来分析劳动分工的。[28]Yang and Borland(1991)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基于中间产品种类的扩展,而且基于单个行为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在他们的框架内,每个行为人都是生产者兼消费者,具有Cobb-Douglas形式的效用函数,劳动分工的深化则表现为行为人出售和购买的产品在其生产和消费的产品中的份额的提高。
在杨小凯和博兰德的模型中,行为人与他人进行贸易的动力来自于多样化的消费偏好与递增报酬的生产技术之间的矛盾:行为人专业化于某种物品的生产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但是却会丧失多样化消费的收益。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是行为人之间展开劳动分工,然后相互交换产品。这种劳动分工受制于两个因素:行为人的人数与交易费用。
Kim and Mohtadi(1992)指出,博兰德-杨模型把劳动分工视为不同工人生产不同产品,其结果是,工人生产率随同一产品的产出水平增加而增加。在Kim- Mohtadi模型中,生产率不是随各种产品生产的间接增加而增加,而是随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劳动专业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这种劳动专业化是以集约性的人力资本与粗放性人力资本的区分为基础的,前者是在既定生产活动中提高工人生产率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后者是使工人在各种生产活动中更具有适应性的一般知识存量,因而提高专业化即意味着具有更多的集约性人力资本和较少的粗放性人力资本。Kim,S.and Mohtadi强调,即使没有技术变化或边干边学,但只要提高这种劳动专业化,长期经济增长就是可能的。
Becker and Murphy(1992) [29]一方面克服了博兰德-杨模型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展中的作用的缺陷,继承了自Arrow以来的知识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指出劳动分工不仅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那样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协调成本”以及可获得一般知识的数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
4、政府部门公共开支、税收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
政府的作用是解释持久而广泛的人均收人和经济增长率跨国差异的根源。政府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增长奇迹”,也可以使一国陷入“Malthus陷阱”。通过税收和公共开支,政府可以影响经济个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Barro(1990)使用了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概念,他假定政府向每个生产者提供公共服务[30](即政府支出),强调政府服务是与私人投人一样的生产性支出,如果离开了它的作用,私人的生产投入只会具有递减收益,而一旦生产性政府服务进人,生产就具有不变规模收益。从而持续增长就成为可能。在这里,政府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政府活动被完全内生化了。政府可选择最优的税收和生产性支出,刺激个人对公共服务的潜在需要,实现持续的人均消费增长。政府维护经济基础和保护财产权力的职能对个人的资本积累是很重要的,另外,自利的政府肯定会降低消费增长率和福利。
Jorgenson和恽坤阳发表了《税收改革和美国经济增长》(1990)一文,利用实际观察数据和估计值来评估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估计1986年美国实际采用的税收使国民财富增加了2.8%,提高了非现世(atemporal)资源的分配效率。但是,根据1986年总统原定的税收计划,税收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因此他们预测增税的潜在可能会阻碍福利的提高。
King-Rebelo模型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表明,税收对国民福利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非常大。以美国的数据分析为例,所得税率上升10%,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大约1.6%。这是因为所得税的提高使人们减少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降低了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
5、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积累与国与国差异
Romer(1986)把生产函数中的企业知识视为知识和某种有形资本复合的财物[31],通过国际贸易和开放环境,知识不但可以在不同国家间自由传播,而且与资本相称的知识的外在影响也可扩散到其他国家,从而被知识密集度较低的国家模仿。Lucas(1988)强调各国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不断被强化,形成专业化生产,从而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Lucas(1990)对新古典模型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论断提出了质疑。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假设投入要素的报酬递减,因而相对于发达经济国家,欠发达经济国家资本的报酬率较高,投资品将从富裕国家快速流向贫穷国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Lucas在文章中对此提供了四种可能的答案,即: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外在利益、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垄断。
(三)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关于人力资本的专门计量研究,一些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进行。例如,1930年, L.Dublin and A.Lotka对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现值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人寿保险合理购买量的衡量指标。1935年, J.R.Walash首次对人力资本价值进行了成本估算。1944年, F.Knight集中考察了经济增长中生产知识的社会存量的增进对克服收益递减的作用。
Kendrick(1961;1973)[32]认为:产量是由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所决定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同产量之比,才是说明经济增长源泉的关键。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中,资本和土地是非劳动性生产要素,因此二者可合并,简化为资本。劳动这项生产要素单列。产值的增长一部分来自实际的资本投入量与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另一部分就来自这些投入量的生产率的增加。当产值增长率与实际的生产要素投入量增长率确定后,两者的差额就是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Denison指出:肯德里克虽然在经济增长源泉方面作了上述分析,但并没有确定每一项因素对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做的贡献大小,而Denison则在经济增长源泉分析中对每一项因素的贡献大小(特别是对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33]
60年代与80年代和90 年代的增长理论的最明显的区别是近来的研究更关注于经验含义以及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34]这样的一些应用性工作涉及对更老一些理论的经验含义的引伸,例如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收敛预测。另一些分析则更为直接地应用于最近的内生增长理论,包括递增报酬、R&D活动、人力资本及技术扩散的作用。
跨国数据揭示了政府对一个经济的增长率的双重影响。负面影响包括消费支出(及与之相联系的税收水平)的规模,国际贸易的扭曲以及政治不稳定性。正面影响则涉及对法律规则运作的制度的维护,促进金融制度发展的可能政策,以及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在多数情况下,实证工作并没有对某一项具体的政府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提供强有力的估计,但它确实表明政策总体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通过影响长期增长率,政府行动可以对生活水准造成重大影响。作为推论,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优先领域。
横截面数据揭示出总投资/GDP之比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之间的规律性。这一比例与以教育成就和健康为形式的初始人力资本正相关,也和真实人均GDP水平正相关。然而,一旦人力资本的数量保持不变,其与真实人均GDP就实际上不相关。这意味着投资/GDP必将随着一国发展且增加其人均人力资本而趋于某种程度的上升。
从生育率及人口增长的角度,跨国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规律。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随着真实人均GDP的增加,生育率趋于下降。然而对于那些最穷的国家而言,正如Malthus(1798)所预测的,生育率会随着GDP的上升而上升。在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更为强烈的联系。除最发达国家之外,妇女教育与生育率负相关,而男性教育与生育率正相关。这些力量的净效应是生育率,以及人口增长率,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在某些时期趋于持续下降。外生不变的人口增长率假设——Solow-Swan模型的另一个关键要素——亦违反了这一经验模型。
一旦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固定不变,则许多变量都与真实人均GDP的增长率显著相关。如:增长正向依赖于以教育成就和健康为形式的人力资本的初始数量,负向依赖于政府消费支出与GDP的比例和导致市场扭曲与政治不稳定的政策措施。总投资与GDP之比和增长率强烈正相关,Coe and Helpman(1993)指出在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样本中,研究与开发(R&D)上的投资与生产率高度相关。然而R&D支出与增长孰为因,孰为果仍不得而知。
五、小结
正如本文开篇指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只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德所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的集合体。如果说在这样的集合体中要梳理出一条主要的研究脉络是困难的,那么对内生增长理论作一个准确的评价则更为艰难。一种偷懒的办法是或许我们可以引用大师的论断。
借用Sala-i-Martin(2001)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或许是恰当的:内生增长理论16年来最大的进展,在于它的实证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而不是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理论突破。内生增长理论使得我们离真实世界更进了一步,但它并没有改变世界本身。
虽然,小小的一步,有时会使世界看起来是那样的不同。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 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载于《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3、 朱保和:《新增长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Aghion P. and P.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 MIT Press, 1998.
5、 Barro, R.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6、 Barro, R.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1.
7、 Barro, R.J. and J. W. Le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3) 363-394, December 1993.
8、 Barro R. J.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 1998
9、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92.
10、 G.S.Becker and K.M. Murphy.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 J]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4): 1137-1160.
11、 Becker,G.S., Murphy,K.M., and Tamura,R.,1990: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 pt.2, pp.s13-137
12、 Cass, D.,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uly 1975
13、 Dixit, Avinash K. and Joseph E.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June 1977. pp. 297-308.
14、 Dowrick, S. and M. Akmal, "Contradictory Trends in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A Tale of Two Biases", mimeo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rch 2001.
15、 Durlauf, S. and D. Quah, "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19W6422, February 1998, in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J. Taylor and M. Woodford
16、 Fujita M., Krugman P., Venables A.J.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Galor, O. and D. N. Weil,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the Malthusian Regime to Eds, North Holland, forthcoming, 2000.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17、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M.I.T. Press, 1991.
18、 Hansen, G. D. and E. C. Prescott, "Malthus to Solow", NBER Working Paper # 6858, 1998.
19、 R. F. Harrod,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Economic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Policy, Macmillan, London, 1948.
20、 Michel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and the Mixe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21、 Jones, C. I, "R&D Bas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95, vol. 103: (4) 759-784
22、 Jones, C. I.,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ummer 1997
23、 Jones, C. I., "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1999.
24、 Jones, L., and R. Manuelli, "A Convex Model of Equilibrium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5):1008-1038.
25、 Kim, S. and Mohtad, H., 1992, Labor Specializ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May), No.2, pp.404-408.
26、 Koopmans, T. C.,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Growth", in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North Holland, 1965.
27、 Kremer, M.,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 August 1993, 681-716.
28、 Kremer, M, A. Onatski and J. Stock, Reaching for Prosperity? NBER Working paper 8250, April 2001.
29、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 1988, (22):3-42.
30、 Lucas, R. 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31、 Mankiw, N.G., D. Romer and D.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2.
32、 Matsuyama, K. "Increasing Retur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1, vol. 106, pp. 617-650
33、 Perotti, R.,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 2, pp. 149-87, June 1996
34、 Quah, D.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Economic Journal, July 1996.
35、 Quah, D. "Empirics for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Polariz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Convergence Club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 1997.
36、 Ramsey, F.,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 Journal, 1928.
37、 Rebelo, S., "Long Run Policy Analysi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38、 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39、 Romer, P.,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40、 Romer, P. "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Ideas and Producing Idea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1992, supplement to the 21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93, 63-91.
41、 Schultz, T. Paul, (1998),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Income in the World: How it
42、 Solow,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J.E., 1956, PP, 65-94.
43、 Summers, Robert and Heston, Alan. (1988). A new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price levels estimates for 130 countries, 1950-1985,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4(1), March, 1-25.
44、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1956, PP.334-61.
45、 Alywn Young. Invention and bounded learning by doing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3):443-472.
46、 Xiaokai Yang and Jeff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9,No 3(June 1991),PP.460-482
*特别感谢导师刘树成所长和左大培研究员对于本文选题、研究思路及框架所提出的有意义的建议与指导;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钢明研究员、王诚研究员、赵志君副研究员,在与他们的讨论中,作者获得极大的启发;与朴商天博士、王劲松博士、李勇坚博士所进行的讨论对于本文很多问题的思路形成亦有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中所有错误与遗漏将由我本人负责。
[1]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对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理论作一个述评,本文所关注的,是经济长期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以人力资本内生化为主线的内生增长理论。另外,虽然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数理化的典范,本文还是不倾向于作一个技术性的说明,对技术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2]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了现在所讨论的人力资本问题。萨伊突出探讨了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经营管理者(企业家)的创新性人力资本的基本问题。穆勒论述了家庭、教育和医疗卫生在人力资本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李斯特则在“精神资本”概念下强调了人力资本的精神存量及教育对国家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瓦尔拉斯认为,资本可分为“土地资本”、“人力资本”和“狭义资本”(即物质资本)。他把人力资本等同于人本身,在量上则等同于“人口的数目”,而且把它看作是一种无须人工所产生的“自然”资本。庞巴维克坚决反对将资本概念泛化,去指代土地和劳力。
作为完整的理论分支的人力资本理论,则是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解释“增长剩余” 的学术和实践背景下开始形成和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主要是T.W.Schultz和Garye Becker。此外, Mr. Friedman、Jacob Mincer、Sherwin Rosen、John Kendrick、Herman Miller等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对人力资本理论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3]至少有三个因素导致了劳动分工在经济学中的边缘化。首先,它无法“在技术上”被证实,或者说,无法用数学模型来进行严格的表述。其次,劳动分工蕴涵了递增报酬,而递增报酬与竞争均衡的不相容正是斯密困境产生的根源(Stigler,1951)。递增报酬必定会导致垄断,认同它会给瓦尔拉斯均衡以致命的打击。最后,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劳动分工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至少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因为主流学派的核心是价格理论,也就是在给定经济结构下的资源配置,而劳动分工则更倾向于是一个生产技术管理问题(参见程炼,2002)。
[4] 参见朱保和(2000)
[5] Solow模型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划分了增长率效应和水平效应。水平效应是经济系统参数变化只引起产出水平发生变化而不引起均衡增长率发生变化,增长率效应是经济系统参数变化引起均衡增长率发生变化。Solow在他1956年的文章中指出储蓄的变化是水平效应。较高的储蓄率所导致的结果不是持续的较高的增长率,而是持续的较高的人均产出。
[6] 增长核算的研究表明资本存量和劳动的增长不能够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未被解释的那部分用技术进步来解释。Solow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分析方法, 并应用这种分析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增长,另外87.5%的产出增长被归为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余数(Residual),从而确立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然而,矛盾之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置于增长过程的核心地位而同时否认经济分析可以说明技术进步过程。因为,根据新古典理论,总产出由劳动和资本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没有剩余用来补偿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一种解释是把技术进步看作由政府通过支持基础研究而提供的公共商品。毫无疑问,战后美国经济可以为这种观点多少提供些佐证。但是,如果用来说明战前美国经济或者其它国家就有些勉强。而且,即使在战后美国,私人企业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研究开发。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无法解释。
[7] Barro R. J.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 1998。
[8]事实上,政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这个观点早已经被经济学家们接受。经济政策既可以通过投资也可以通过资本等中间投入的使用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经济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
[9] Barro R. J.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 1998
[10]因为知识具有非竞争的特征,一个企业利用了一个点子,并不妨碍其他企业的利用。另外一方面企业有动机来对其发明保密以及利用正式的专利保护措施来保护其发明。有关生产率改进的知识因而只会逐渐披露,创新者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有竞争优势。在一个分权框架中,这个个体优势对于发明创造努力程度的激励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这一个框架中产生的企业之间的这类互动却不能被标准的完全竞争模型所充分描述。这里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即假定所有的发现都是投资的无意识的副产品,而且这些发现立即成为共同知识。这一假定容许我们保留完全竞争框架,尽管其结果将被证明不是帕累托最优。
[11]干中学与外溢效应模型意味着对于由单个企业选择的要素Ki和Li而言规模报酬不变。如果在一个企业的水平上适用的是递增报酬,则该模型不能与完全竞争相一致,因为企业为了受惠于规模经济将由动力增长到任意大的地步。通过假设一个企业的技术依赖于总资本存量K而且每个企业都忽略了其自身对这一总量的贡献,我们避免了这一后果。这个规定使得我们能维持完全竞争的假设,当它也意味着竞争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
[12] Romer(1987;1990);Aghion and Howitt(1991)
[13] Barro R. J.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 1998
[14]Schultz( 1986)《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一文无疑是内生增长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直接动因。在该文中,Schultz重新提出杨1928年的经典论文,并将它作了发挥。他认为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到Solow增长模型都是误导的, 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忽略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及特点 ,是忽略了企业家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性质时所作的贡献 结果经济分析完全封闭在收益递减的均衡状态之中,因而迟迟不能建立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Schultz强调,经济增长应该源自专业化、劳动分工和递增收益,尤其强调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递增收益的一个重要源泉。Schultz指出,由于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收益递增可以突破经济增长的任何限制并且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可以允许竞争性均衡的存在。由此Schultz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一般均衡分析可以并且应该用来研究包含人力资本和递增收益在内的经济增长;其二专业化、产业化的人力资本、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必定结伴而行。
[15] Barro R. J.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 1998
[16] Rebelo,S.,1991:Long-Run Policy Analysi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9, No.3, pp. 500 -521
[17]假定生产函数中的投入是物质和人力资本K和H,假设单部门技术既适用于消费品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又适用于人力资本即教育的生产:其中呈现出标准的新古典性质,包括K和H的不变规模报酬——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性质把生产函数写成集约形式:其中。若定义为一个常数,则上式意味着,K为代表了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在内的一种资本品的组合。
[18] 参见朱保和(2000)
[19] 传统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为Marx-Neumann模型,假定经济有资本家和劳动者两大阶级组成,劳动者与资本积累无关,而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第二类模型称为Keynes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假定经济由法人企业的生产部门和劳动者与食利者的家庭部门构成,并且生产部门和家庭部门在不同经济动机驱动下分别决定生产和消费,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第三类模型属于Solow-Swan经济增长模型的扩展形,也称为新古典学派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它假定经济由抽象的理性经济主体构成,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的理性行为选择储蓄和消费,进而决定经济增长的途径。
[20] Arrow(1960)认为学习效果的存在使得人们通过连续地从某种生产活动而获得新的知识或技术成为可能。实际上,为获得新的知识或技术而连续地从事某种生产活动必然需要劳动或其他资源的投入,因此就会出现为实现一定的技术进步,社会到底需要投入多少劳动资源才是最优的问题。
[21] Lucas,R.,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22..
[22] Lucas(1988)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动态性质,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动态性质的研究主要由Mulligan and Sala-i-Martin(1993)等进行展开。
[23] 需要指出的是,Lucas(1988)中采用的人力资本概念和Rome(1987)是不一样的。Romer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对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累积效应的测量。这个定义比卢卡斯等人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范围窄些,后者还包含了Romer所指的知识。
[24] 参见Barro(1998)
[25] Romer(1987,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Young,Alwyn(1993)
[26] Xiaokai,Young(1998) ;Becker and Murphy(1992);Kim,S.and Mohtadi(1992)
[27] 可以解释为研发费用。
[28] 参见Xiaokai,Young(1998)
[29] G.S.Becker and K.M. Murphy.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 J]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4): 1137-1160.
[30]Barro and Sala-i-Martin()指出,最优的税收政策依公共服务的特征而定,进而把公共服务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共提供的私人产品,它是竞争且排他性的公共服务;一类是公共提供的公共产品,它是非竞争性且非排他性的公共服务;一类是会产生过度消费的公共产品,它是竞争且有某种程度的非排他性。这三类不同的公共服务对增长都具有生产性效应,但各自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
[31] Arrow认为知识由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体现。
[32]Kendrick, J.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Princeton,1961
[33]据Denison的计算,从1909年到1929年,美国生产量的年增长率为2.82%,劳动力质量平均每年提高0.56%,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12%归功于劳动的质量的提高。从1929年到1957年,美国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2.93%,劳动力的质量平均每年提高0.93%,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23%归功于劳动的质量的提高(Denison, E.F. Th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1962)。另据Denison的计算,从1950年到1962年,美国生产量的年增长率为3.32%,劳动力的质量平均每年提高0.62%,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15%归功于劳动的质量的提高。从劳动力质量提高在西方其他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美国居于首位(Denison, E.F. Why Growth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1967)。
[34]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