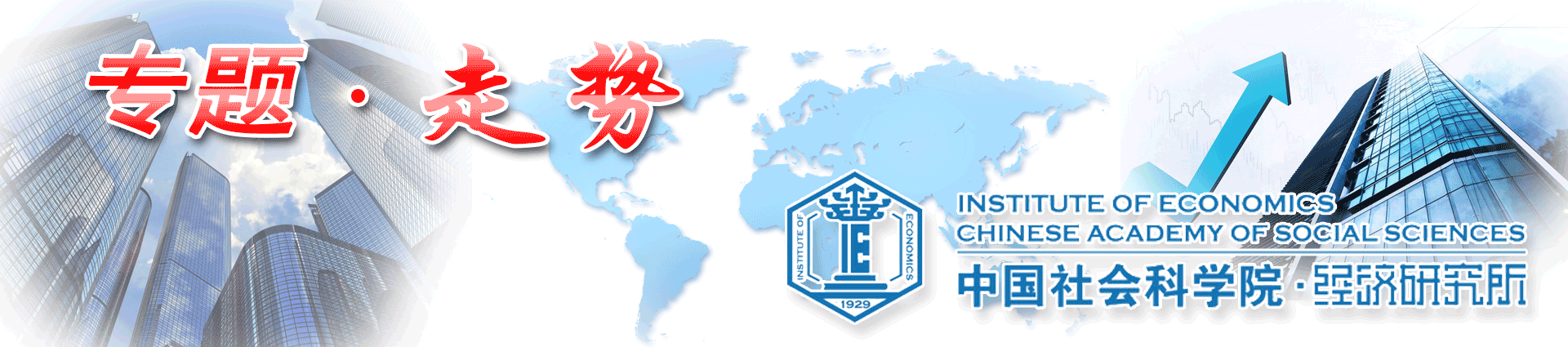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91期(总第1213期) 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上接第89期)
三、欧美面临的衰落与困境
美国该学会面对衰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一位退休的英国外交官声称是他首创了“衰落管理” (the management of decline)这个词组,用来描述1945年之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但是,现代美国还没有。如果美国能够公开承认其全球实力在衰落,那么就应采取哪些对策展开理智讨论就会容易得多。拒绝承认事实不是可取的策略。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曾说过,他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全球第一的地位。即便如此,对手们还严厉批评他有“衰落主义”心态。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指责总统欣然接受美国的衰弱:“衰落不是一种状态,”他表示,“衰落是一种选择。”顽强抵制“衰落主义”的并非只有极右人士。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老前辈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谈论美国的衰落视为知识界一时的风尚——可以和早些年认为日本正超过美国的“妄想症”相提并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的副标题是“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以及我们如何东山再起” (What went wrong with America – and how it can come back)。
主流讨论不能容忍的一些观点是,认为美国可能无法“东山再起”,以及美国实力的衰落既不是一时的风尚,也不是选择,而是一个事实。诚然,与1945年后大英帝国实力的削弱相比,美国的相对衰落很可能远不会来得那么突然。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无疑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军事和外交强国。但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很可能2020年就是中国超车的时候。当然,中国自身也的确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这意味着——即便中国增长率显著下降——终有一天,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
即便失去经济主导地位,美国在军事、外交、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影响力能确保其全球最重要政治强国的地位不变——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尽管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是一回事,但两者无疑联系紧密。随着中国和其它强国在经济上崛起,它们势必会限制美国在世界上独行其是的能力。
正因如此,美国需要理性讨论“相对衰落”(relative decline)意味着什么,也正因如此,英国的经历——虽与美国迥然不同——或许仍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教训。
英国在1945年之后发现,国力衰落与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维系国家安全完全是可以并存的。衰落不一定意味着和平与繁荣的终结。但衰落确实意味着做出选择和建立同盟。在预算赤字高企和中国实力上升的时代,美国必须更深入地思考哪些是自己的要务。希拉里•克林顿最近曾坚称,美国在亚洲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尽管美国必然为此支付了高额军费。这没什么不好,但对于国内开支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几位政客准备进行相关讨论。相反,他们又开始拿那些称颂美国之“伟大”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口号安慰自己,尤其在共和党人当中。
拒绝考虑美国衰落讨论的人,实际上可能会加快美国衰落的进程。以现实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受到威胁,应该能够促进美国在从教育改革到预算赤字等各个领域采取果断行动。华盛顿无休止的政治作态,反映出一定程度的自满情绪——相信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是那么牢不可破,因而敢于放纵自己,例如今年夏天政府频临违约的那场闹剧。
如果美国相对衰落的问题不能得到恰当的讨论,美国的公共舆论对于迎接一个新时代就可能准备不足。其结果是,对于美国在国内外遭受的挫败,公众的反应不大可能是冷静和果断的,而更可能是愤怒和荒谬的——这将助长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称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
因为事实是,衰落管理与心理学的关系,和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同样密切。在1945年,二战胜利的余辉使英国管理衰落任务变得容易了许多。英国的调整也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新的全球霸主是美国,而美英两国通过语言、血统和共同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美国把权力让给中国就会艰难得多——尽管这次交接和英国经历的交接相比将远没有那么彻底。
如今的英国人差不多已学会了享受失败。他们大量购买讲述失败的书籍,书名类似《失败英雄传》(The Book of Heroic Failures)。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当一只英国足球队失利时,支持者们会高唱,“我们是垃圾,我们知道自己是垃圾”。我看这种习惯不太可能在美国流行起来。在管理衰落的时候,自我贬低只是可选项。
消灭“不平等”不可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在一篇评论中说,信用紧缩发生之前,有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右翼在经济论战中取胜,左翼则赢得了文化辩论。然而,左翼似乎还赢得了第三种争论——语言学争论。我指的是,他们使用“不平等”这个词语来表述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平等应是常态,如偏离了平等,就需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如今这个问题再度引起热议。许多富有的商人,包括基金经理沃伦•巴菲特,似乎对自己的收入怀有负罪感,而且还呼吁政府向他们所属的群体征收更高的税款。官方统计人员不断发布有关不平等变化情况的研究报告。上届(英国)工党政府留下了一部骇人的《平等法》(Equalities Act)。根据某些解读,该法主要是为了打击种族与性别歧视;但根据另一些解读,该法的干预性更强。
布里坦还驳斥了一些反对追求实质平等的糟糕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平等主义立法将导致稀有人才移民。以这种立法为基础就会将道德高地拱手相让于人。这样一来,非平等主义立场便只能依赖划分各国的边境线,在任何认真促进平等的国际性努力面前都会土崩瓦解。另一个糟糕的观点是,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反应了个人的价值。即便果真如此,这也是一种不充分的反应。作者引用了F•A•哈耶克(F.A. Hayek)的一段话:“至于自己的才华是世间罕有,还是稀松平常,个人即使想要改变也几乎无计可施。美好的心灵或甜美的嗓音,美丽的面孔或灵巧的双手,敏捷的头脑或迷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和个人的努力无关……在上述所有方面,一个人为我们提供的服务(他也借此获得报偿)所具有的价值,与我们所称的道德品行或‘美德’关系甚小。”。
唯一令人信服的反对平等主义政策的观点,其出发点是否认所有收入和财富最初都归国家所有。哈佛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对此阐述得很清晰:“我们不是孩子,等着分得一块馅饼。没有集中分配这一说。每个人所得到的东西,都是别人为了交换另一样东西而给他的,或是赠送给他的礼物。在自由社会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资源,获得新资源的方式是人们的自愿交换或者行动。”
布里坦指出,我们不是把一个固定的数量分配给每个人;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活动使馅饼增大。但这绝不是:其他人应把增大的馅饼当作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财产权的真正内容,以及规范财产权转让和保护的规则,都是集体强制原则和决定的产物,而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这些原则和决定。然而,这种资格赋予国家的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权利,而不是所有收入都属于国家的主张。
有人说,在过去三十年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向最顶层人口集中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同时,最底层人口的地位(至少是相对地位)在下降。声称巴菲特等人愿意捐出多少财富是他们的自由,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法。巴菲特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我将自愿捐赠x,但如果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其他有钱人按比例捐赠的话,我会捐赠x+y。”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谁是受益者?”仅仅想要羞辱富人一番,反映出的是羡慕和嫉妒。大多数不平等指数,无论是听上去挺有技术含量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ent),还是体现最顶层10%人口和最底层10%人口收入之比的“90/10”比例,都会显示出对富人的没收性税赋明显增多,哪怕由此增加的收入被抛进大海。无论我们提出什么建议,是提高对富人征税额、还是以其它方式惩罚富人,都应该明确指出这么做如何能让最底层的10%民众、甚至是中间阶层市民收益。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重印一篇名为《要再分配,不要平等》(Redistribution: Yes. Equality: No.)的文章。或许现在这篇文章能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了。
欧洲左派的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什么样的政治哲学适合欧洲左翼政党?这些政党有始终如一的理论依据吗?对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它们既无法形成任何前后一致的认识,也不知如何应对,更是使这个问题备受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坚定推崇个人主义的强大美国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他所著的《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发展了洛克(Locke)和卢梭几个世纪以前创立的社会契约论。罗尔斯邀请他的读者思考,当他们处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时——这时他们对自己将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经济或政治地位一无所知——能够达成怎样的契约。
罗尔斯认为,风险厌恶者将会选择平等的经济秩序。这种个人主义的契约方法论还有其他的追随者,比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运用它得出了更为保守的结论。基于契约论和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自始至终最为坚定地反对这种方法论的一群人包括: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大西洋的欧洲一侧,反对者则有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和约翰•格雷(John Gray)。这些学者认为,个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群的产物,根据这种理念,社会能够在“无知之幕”背后构筑起来的想法便变得毫无道理。我们可以为这一学派贴上社群主义的标签,不过其成员对这种称谓抱有异议,甚至根本否认有这样一个学派存在。
在所有政党之中,都存在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红色托利(Red Tory)用来指代菲利普•布朗德(Phillip Blond)这样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阵营中的社群主义者,蓝色工党(Blue Labour)则指格拉斯曼这样工党中的社群主义者。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差别,也能够用来描述政治领导人的不同执政方法,尽管领导人自己对于权威文本或许并不怎么了解。托尼•布莱尔和戴维•卡梅伦是本能的社群主义者,戈登•布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则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
保守党的两难境地源自该党派与两个不同派系的长期同盟,一派是推崇传统和社会共识的伯克(Burke)派保守主义者,一派是激进而对抗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保守党联盟中,一直到撒切尔夫人掌权之时,前者大体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卡梅伦的“大社会”运动则试图扭转这种平衡关系。
工党的两难抉择则出现得较晚。温和的左翼知识分子牢牢抓住罗尔斯主义路线。它与表达权利(人权及经济权利)的新语言形成共鸣,并为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另一种话语。
但大部分选民并不知道,社群主义不再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宠儿。从来就极少有选民对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感兴趣,对于有关权利的新论调,他们也同样不感兴趣。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并不是基于对权利主张的认可,而是基于团结、同情和赏罚得当的考虑。
于是,左翼政党内部划分为两派,一派珍视人权、多元文化主义和环境,另一派就是左翼政党的其余大多数支持者。后者关心的是人身安全和经济保障,对坚持特定价值观的种族或宗教群体持怀疑态度。对他们而言,环境恶化指的是他们所生活的社群环境的恶化。已经隐退的布朗接受达菲女士(Mrs Duffy)的诘问时,就被迫直面这种分岐。达菲女士是一位有不满情绪的选民,布朗对她出言羞辱,却未能应对她提出的问题。
四、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危机让马克思主义复兴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几乎每一次影响商业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期间,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还是马克思说的对。”几年前,人们曾看到萨科齐颇有几分卖弄地攥着一本《资本论》,而最近,包括鲁里埃尔•鲁比尼和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在内的金融大师们,也都曾撰文提及这位共产主义思想家。而当经济复苏时,这种声音就会消失,下次再发生经济衰退时又会再次出现。这种声音第一个错误之处在于,它其实跟卡尔•马克思没有多大关系。
马克思最初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他对黑暗时代(Dark Ages)之后的历史划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点儿像英国工党旧党章第四款(Clause IV)中构想的某种极端形式,所有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也与其后来的含义没有任何关系。它本来指的是一个乌托邦,在这里一个短暂的工作日便能提供整个社会所需,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上午狩猎、下午捕鱼、晚上讨论哲学”。正是这种社会的愿景,让许多本来可能逃离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想主义者们留了下来。
我发觉这种愿景比英国历史学家的典型观点更为有趣,他们研究的主题只是一件事跟着另一个事件。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版本也存在很多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始自15世纪意大利的诸共和国?在欧洲一些地区,工业革命到19世纪开始后很久才真正开始,资本主义在那里是不是迟迟没有出现?而俄国在尚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时,马克思在那里就有了数量惊人的信徒,这又该如何解释?马克思晚年时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指什么?基本上是在说,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扩大,而贫穷的沦为无产阶级的人民却无力购买。近20年前,苏联体制瓦解之后,这个理论似乎就过时了。然而随着财富和收入集中度的上升,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詹(Raghuram Rajan)就曾指出,最近的信贷体系崩溃的部分原因在于,真实工资水平增长停滞,从而鼓励人们举债。
然而,即使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解决手段也是错误的。财富再分配的理由关乎道德。如果资本主义唯一的错误之处在于群众购买力不足,那么解决办法肯定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设想的用直升机撒钱。就此而言,我们不太需要一场政治变革,而是需要一场思想变革,也就是说要抛弃对于预算平衡的笃信。
正如A•J•P•泰勒(AJP Taylor)在他为企鹅版《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序言中所暗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德语世界的一大特征。其最有趣的发展出自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之手,他的长期贡献在于其著作《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kapital)。他在书中提醒读者注意一个险恶的新特点:工业卡特尔化的背后,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崛起。可是他没有预见到大量人造货币跨越国界快速流动的更大重要性,各国中央银行正在绞尽脑汁地想要重启全球经济,此时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恰逢其时。
马克思的预言会成真吗?
专栏作家托尼•杰克逊说,当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在西方世界各处安营扎寨时,有人形容道,卡尔•马克思的魂灵正在这些帐篷间游荡、并赞许地点着头。马克思虽然从他的前提假设出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那些假设却可能具有启发意义。比如说他的这个观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因为它会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
英国央行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最近一次演讲中使用了类似的词汇。那次演讲的大意是,上世纪金融业的多数有害发展都来自于银行“打破资产负债表枷锁”的渴望。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后半段,南非主要企业积极与流亡海外的革命者合谋推翻该制度——这一事实似乎有些荒谬。但按照种族隔离制度的逻辑,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无权投票,那么他们也无权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南非企业却极其缺乏熟练劳动力。因此,对南非的资本而言,种族隔离制度已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它必须灭亡。
银行的例子则不那么光彩。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直到最近受挫为止)极其的简单,那就是必须扩大规模、同时承担更高的风险。
这两个目标当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正是多年来银行抛弃无限责任制、进行整合、举债经营、追逐波动性和其它很多活动背后的原因。
引用一些霍尔丹提供的数据来说明。19世纪80年代,英国银行总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在泡沫处于顶峰的时候,这一比例曾达到500%。至于整合,20世纪初英国三大银行的资产相当于GDP的7%。到20世纪末,这一比例变成了75%。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200%。杠杆率则从19世纪的3倍到4倍升至泡沫时期的30倍。股本回报率也不出所料地从较低的个位数升至泡沫顶峰时期的30%。
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最近的一些创新或许原本是为了减少风险。例如,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对机构储蓄加以利用并将违约风险分散到更广泛金融体系的一种巧妙方法。根据最初的设想,信贷衍生品的用途也与此相同。当然,最终的结果并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出于对风险的追求,银行设法将这两种创新合并了一个邪恶的组合。这样,抵押贷款支持衍生品便成为此次危机的触发器。
这种疯狂的冒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泡沫时期,银行股本仅相当于银行资产的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根据股本回报率向首席执行官支付报酬,那么其对经营行为的扭曲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杠杆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波动性也将受到鼓励。
另一个原因当然是,由于银行被视为“大到不能倒”,因此这些风险是不对称的。但我们在这里必须当心一点。经济学家们往往假定:金融参与者永远都是理性的;因此,如果我们解决了“大到不能倒”的问题,过度的冒险行为就会消失。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霍尔丹的计算,在美国,银行持股比例最大的三家机构(按降序排列)是雷曼、贝尔斯登和美林。银行董事会没有按照股东的最大利益行事,格林斯潘曾对此天真地感到意外,并因此遭到外界的嘲笑。但是,如果银行的老总们最终甚至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事,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人性中固有的顽疾之一。因此,我们肯定会在下一次泡沫时再次遭遇它。
毫无疑问,那一天距我们还很遥远。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萧条的威胁意味着,我们在修复银行业体系时切忌过于冲动,以免导致银行无法履行原本的职能。但我们终有一天会摆脱这一威胁。届时会再次出现很多的声音坚称,规模庞大且敢于冒险的银行对于资本主义至关重要。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前进不可阻挡。就这一点而言,让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再次证明他是错的吧。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91期(总第1213期)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91期(总第1213期) 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上接第89期)
三、欧美面临的衰落与困境
美国该学会面对衰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一位退休的英国外交官声称是他首创了“衰落管理” (the management of decline)这个词组,用来描述1945年之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但是,现代美国还没有。如果美国能够公开承认其全球实力在衰落,那么就应采取哪些对策展开理智讨论就会容易得多。拒绝承认事实不是可取的策略。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曾说过,他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全球第一的地位。即便如此,对手们还严厉批评他有“衰落主义”心态。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指责总统欣然接受美国的衰弱:“衰落不是一种状态,”他表示,“衰落是一种选择。”顽强抵制“衰落主义”的并非只有极右人士。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老前辈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谈论美国的衰落视为知识界一时的风尚——可以和早些年认为日本正超过美国的“妄想症”相提并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的副标题是“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以及我们如何东山再起” (What went wrong with America – and how it can come back)。
主流讨论不能容忍的一些观点是,认为美国可能无法“东山再起”,以及美国实力的衰落既不是一时的风尚,也不是选择,而是一个事实。诚然,与1945年后大英帝国实力的削弱相比,美国的相对衰落很可能远不会来得那么突然。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无疑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军事和外交强国。但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很可能2020年就是中国超车的时候。当然,中国自身也的确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这意味着——即便中国增长率显著下降——终有一天,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
即便失去经济主导地位,美国在军事、外交、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影响力能确保其全球最重要政治强国的地位不变——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尽管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是一回事,但两者无疑联系紧密。随着中国和其它强国在经济上崛起,它们势必会限制美国在世界上独行其是的能力。
正因如此,美国需要理性讨论“相对衰落”(relative decline)意味着什么,也正因如此,英国的经历——虽与美国迥然不同——或许仍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教训。
英国在1945年之后发现,国力衰落与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维系国家安全完全是可以并存的。衰落不一定意味着和平与繁荣的终结。但衰落确实意味着做出选择和建立同盟。在预算赤字高企和中国实力上升的时代,美国必须更深入地思考哪些是自己的要务。希拉里•克林顿最近曾坚称,美国在亚洲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尽管美国必然为此支付了高额军费。这没什么不好,但对于国内开支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几位政客准备进行相关讨论。相反,他们又开始拿那些称颂美国之“伟大”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口号安慰自己,尤其在共和党人当中。
拒绝考虑美国衰落讨论的人,实际上可能会加快美国衰落的进程。以现实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受到威胁,应该能够促进美国在从教育改革到预算赤字等各个领域采取果断行动。华盛顿无休止的政治作态,反映出一定程度的自满情绪——相信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是那么牢不可破,因而敢于放纵自己,例如今年夏天政府频临违约的那场闹剧。
如果美国相对衰落的问题不能得到恰当的讨论,美国的公共舆论对于迎接一个新时代就可能准备不足。其结果是,对于美国在国内外遭受的挫败,公众的反应不大可能是冷静和果断的,而更可能是愤怒和荒谬的——这将助长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称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
因为事实是,衰落管理与心理学的关系,和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同样密切。在1945年,二战胜利的余辉使英国管理衰落任务变得容易了许多。英国的调整也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新的全球霸主是美国,而美英两国通过语言、血统和共同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美国把权力让给中国就会艰难得多——尽管这次交接和英国经历的交接相比将远没有那么彻底。
如今的英国人差不多已学会了享受失败。他们大量购买讲述失败的书籍,书名类似《失败英雄传》(The Book of Heroic Failures)。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当一只英国足球队失利时,支持者们会高唱,“我们是垃圾,我们知道自己是垃圾”。我看这种习惯不太可能在美国流行起来。在管理衰落的时候,自我贬低只是可选项。
消灭“不平等”不可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在一篇评论中说,信用紧缩发生之前,有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右翼在经济论战中取胜,左翼则赢得了文化辩论。然而,左翼似乎还赢得了第三种争论——语言学争论。我指的是,他们使用“不平等”这个词语来表述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平等应是常态,如偏离了平等,就需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如今这个问题再度引起热议。许多富有的商人,包括基金经理沃伦•巴菲特,似乎对自己的收入怀有负罪感,而且还呼吁政府向他们所属的群体征收更高的税款。官方统计人员不断发布有关不平等变化情况的研究报告。上届(英国)工党政府留下了一部骇人的《平等法》(Equalities Act)。根据某些解读,该法主要是为了打击种族与性别歧视;但根据另一些解读,该法的干预性更强。
布里坦还驳斥了一些反对追求实质平等的糟糕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平等主义立法将导致稀有人才移民。以这种立法为基础就会将道德高地拱手相让于人。这样一来,非平等主义立场便只能依赖划分各国的边境线,在任何认真促进平等的国际性努力面前都会土崩瓦解。另一个糟糕的观点是,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反应了个人的价值。即便果真如此,这也是一种不充分的反应。作者引用了F•A•哈耶克(F.A. Hayek)的一段话:“至于自己的才华是世间罕有,还是稀松平常,个人即使想要改变也几乎无计可施。美好的心灵或甜美的嗓音,美丽的面孔或灵巧的双手,敏捷的头脑或迷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和个人的努力无关……在上述所有方面,一个人为我们提供的服务(他也借此获得报偿)所具有的价值,与我们所称的道德品行或‘美德’关系甚小。”。
唯一令人信服的反对平等主义政策的观点,其出发点是否认所有收入和财富最初都归国家所有。哈佛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对此阐述得很清晰:“我们不是孩子,等着分得一块馅饼。没有集中分配这一说。每个人所得到的东西,都是别人为了交换另一样东西而给他的,或是赠送给他的礼物。在自由社会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资源,获得新资源的方式是人们的自愿交换或者行动。”
布里坦指出,我们不是把一个固定的数量分配给每个人;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活动使馅饼增大。但这绝不是:其他人应把增大的馅饼当作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财产权的真正内容,以及规范财产权转让和保护的规则,都是集体强制原则和决定的产物,而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这些原则和决定。然而,这种资格赋予国家的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权利,而不是所有收入都属于国家的主张。
有人说,在过去三十年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向最顶层人口集中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同时,最底层人口的地位(至少是相对地位)在下降。声称巴菲特等人愿意捐出多少财富是他们的自由,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法。巴菲特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我将自愿捐赠x,但如果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其他有钱人按比例捐赠的话,我会捐赠x+y。”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谁是受益者?”仅仅想要羞辱富人一番,反映出的是羡慕和嫉妒。大多数不平等指数,无论是听上去挺有技术含量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ent),还是体现最顶层10%人口和最底层10%人口收入之比的“90/10”比例,都会显示出对富人的没收性税赋明显增多,哪怕由此增加的收入被抛进大海。无论我们提出什么建议,是提高对富人征税额、还是以其它方式惩罚富人,都应该明确指出这么做如何能让最底层的10%民众、甚至是中间阶层市民收益。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重印一篇名为《要再分配,不要平等》(Redistribution: Yes. Equality: No.)的文章。或许现在这篇文章能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了。
欧洲左派的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什么样的政治哲学适合欧洲左翼政党?这些政党有始终如一的理论依据吗?对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它们既无法形成任何前后一致的认识,也不知如何应对,更是使这个问题备受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坚定推崇个人主义的强大美国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他所著的《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发展了洛克(Locke)和卢梭几个世纪以前创立的社会契约论。罗尔斯邀请他的读者思考,当他们处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时——这时他们对自己将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经济或政治地位一无所知——能够达成怎样的契约。
罗尔斯认为,风险厌恶者将会选择平等的经济秩序。这种个人主义的契约方法论还有其他的追随者,比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运用它得出了更为保守的结论。基于契约论和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自始至终最为坚定地反对这种方法论的一群人包括: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大西洋的欧洲一侧,反对者则有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和约翰•格雷(John Gray)。这些学者认为,个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群的产物,根据这种理念,社会能够在“无知之幕”背后构筑起来的想法便变得毫无道理。我们可以为这一学派贴上社群主义的标签,不过其成员对这种称谓抱有异议,甚至根本否认有这样一个学派存在。
在所有政党之中,都存在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红色托利(Red Tory)用来指代菲利普•布朗德(Phillip Blond)这样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阵营中的社群主义者,蓝色工党(Blue Labour)则指格拉斯曼这样工党中的社群主义者。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差别,也能够用来描述政治领导人的不同执政方法,尽管领导人自己对于权威文本或许并不怎么了解。托尼•布莱尔和戴维•卡梅伦是本能的社群主义者,戈登•布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则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
保守党的两难境地源自该党派与两个不同派系的长期同盟,一派是推崇传统和社会共识的伯克(Burke)派保守主义者,一派是激进而对抗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保守党联盟中,一直到撒切尔夫人掌权之时,前者大体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卡梅伦的“大社会”运动则试图扭转这种平衡关系。
工党的两难抉择则出现得较晚。温和的左翼知识分子牢牢抓住罗尔斯主义路线。它与表达权利(人权及经济权利)的新语言形成共鸣,并为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另一种话语。
但大部分选民并不知道,社群主义不再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宠儿。从来就极少有选民对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感兴趣,对于有关权利的新论调,他们也同样不感兴趣。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并不是基于对权利主张的认可,而是基于团结、同情和赏罚得当的考虑。
于是,左翼政党内部划分为两派,一派珍视人权、多元文化主义和环境,另一派就是左翼政党的其余大多数支持者。后者关心的是人身安全和经济保障,对坚持特定价值观的种族或宗教群体持怀疑态度。对他们而言,环境恶化指的是他们所生活的社群环境的恶化。已经隐退的布朗接受达菲女士(Mrs Duffy)的诘问时,就被迫直面这种分岐。达菲女士是一位有不满情绪的选民,布朗对她出言羞辱,却未能应对她提出的问题。
四、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危机让马克思主义复兴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几乎每一次影响商业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期间,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还是马克思说的对。”几年前,人们曾看到萨科齐颇有几分卖弄地攥着一本《资本论》,而最近,包括鲁里埃尔•鲁比尼和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在内的金融大师们,也都曾撰文提及这位共产主义思想家。而当经济复苏时,这种声音就会消失,下次再发生经济衰退时又会再次出现。这种声音第一个错误之处在于,它其实跟卡尔•马克思没有多大关系。
马克思最初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他对黑暗时代(Dark Ages)之后的历史划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点儿像英国工党旧党章第四款(Clause IV)中构想的某种极端形式,所有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也与其后来的含义没有任何关系。它本来指的是一个乌托邦,在这里一个短暂的工作日便能提供整个社会所需,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上午狩猎、下午捕鱼、晚上讨论哲学”。正是这种社会的愿景,让许多本来可能逃离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想主义者们留了下来。
我发觉这种愿景比英国历史学家的典型观点更为有趣,他们研究的主题只是一件事跟着另一个事件。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版本也存在很多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始自15世纪意大利的诸共和国?在欧洲一些地区,工业革命到19世纪开始后很久才真正开始,资本主义在那里是不是迟迟没有出现?而俄国在尚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时,马克思在那里就有了数量惊人的信徒,这又该如何解释?马克思晚年时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指什么?基本上是在说,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扩大,而贫穷的沦为无产阶级的人民却无力购买。近20年前,苏联体制瓦解之后,这个理论似乎就过时了。然而随着财富和收入集中度的上升,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詹(Raghuram Rajan)就曾指出,最近的信贷体系崩溃的部分原因在于,真实工资水平增长停滞,从而鼓励人们举债。
然而,即使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解决手段也是错误的。财富再分配的理由关乎道德。如果资本主义唯一的错误之处在于群众购买力不足,那么解决办法肯定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设想的用直升机撒钱。就此而言,我们不太需要一场政治变革,而是需要一场思想变革,也就是说要抛弃对于预算平衡的笃信。
正如A•J•P•泰勒(AJP Taylor)在他为企鹅版《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序言中所暗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德语世界的一大特征。其最有趣的发展出自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之手,他的长期贡献在于其著作《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kapital)。他在书中提醒读者注意一个险恶的新特点:工业卡特尔化的背后,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崛起。可是他没有预见到大量人造货币跨越国界快速流动的更大重要性,各国中央银行正在绞尽脑汁地想要重启全球经济,此时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恰逢其时。
马克思的预言会成真吗?
专栏作家托尼•杰克逊说,当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在西方世界各处安营扎寨时,有人形容道,卡尔•马克思的魂灵正在这些帐篷间游荡、并赞许地点着头。马克思虽然从他的前提假设出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那些假设却可能具有启发意义。比如说他的这个观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因为它会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
英国央行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最近一次演讲中使用了类似的词汇。那次演讲的大意是,上世纪金融业的多数有害发展都来自于银行“打破资产负债表枷锁”的渴望。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后半段,南非主要企业积极与流亡海外的革命者合谋推翻该制度——这一事实似乎有些荒谬。但按照种族隔离制度的逻辑,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无权投票,那么他们也无权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南非企业却极其缺乏熟练劳动力。因此,对南非的资本而言,种族隔离制度已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它必须灭亡。
银行的例子则不那么光彩。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直到最近受挫为止)极其的简单,那就是必须扩大规模、同时承担更高的风险。
这两个目标当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正是多年来银行抛弃无限责任制、进行整合、举债经营、追逐波动性和其它很多活动背后的原因。
引用一些霍尔丹提供的数据来说明。19世纪80年代,英国银行总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在泡沫处于顶峰的时候,这一比例曾达到500%。至于整合,20世纪初英国三大银行的资产相当于GDP的7%。到20世纪末,这一比例变成了75%。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200%。杠杆率则从19世纪的3倍到4倍升至泡沫时期的30倍。股本回报率也不出所料地从较低的个位数升至泡沫顶峰时期的30%。
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最近的一些创新或许原本是为了减少风险。例如,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对机构储蓄加以利用并将违约风险分散到更广泛金融体系的一种巧妙方法。根据最初的设想,信贷衍生品的用途也与此相同。当然,最终的结果并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出于对风险的追求,银行设法将这两种创新合并了一个邪恶的组合。这样,抵押贷款支持衍生品便成为此次危机的触发器。
这种疯狂的冒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泡沫时期,银行股本仅相当于银行资产的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根据股本回报率向首席执行官支付报酬,那么其对经营行为的扭曲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杠杆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波动性也将受到鼓励。
另一个原因当然是,由于银行被视为“大到不能倒”,因此这些风险是不对称的。但我们在这里必须当心一点。经济学家们往往假定:金融参与者永远都是理性的;因此,如果我们解决了“大到不能倒”的问题,过度的冒险行为就会消失。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霍尔丹的计算,在美国,银行持股比例最大的三家机构(按降序排列)是雷曼、贝尔斯登和美林。银行董事会没有按照股东的最大利益行事,格林斯潘曾对此天真地感到意外,并因此遭到外界的嘲笑。但是,如果银行的老总们最终甚至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事,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人性中固有的顽疾之一。因此,我们肯定会在下一次泡沫时再次遭遇它。
毫无疑问,那一天距我们还很遥远。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萧条的威胁意味着,我们在修复银行业体系时切忌过于冲动,以免导致银行无法履行原本的职能。但我们终有一天会摆脱这一威胁。届时会再次出现很多的声音坚称,规模庞大且敢于冒险的银行对于资本主义至关重要。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前进不可阻挡。就这一点而言,让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再次证明他是错的吧。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91期(总第1213期)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